2014年11月29日 星期六
守財奴的猙獰面目
我正為倫敦女王收藏的 “金”(Gold)展覽的藝術作品寫評論
特別喜愛這一幅16世紀的畫
“金” 總給人一種輝煌亮麗之感 但也有醜陋的一面...
描繪收稅人的貪婪 守財奴的猙獰面目 ..... 多像當今的銀行家呢!
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
2014年11月25日 星期二
Niall Ferguson
面對西方氾濫的馬克斯文化
Niall Ferguson
之前念過他幾本書
也去聽過他的演說
算是我在現今知識份子與歷史學家之中
少數能仰慕的人
這是他2011年在蘇格蘭的演說
約20多分鐘....
很精彩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1914年聖誕節休戰
最近 英國的 Sainsbury's 拍了這樣的一個廣告 提醒一百年前德軍與英軍在戰爭時的感人故事
發生在1914年的聖誕節......
我剛好也讀到了Private Frederick W. Heath (英國軍人)寫的一封信
從頭到尾
娓娓道出當時的情景:
The night closed in early - the ghostly shadows that haunt the trenches came to keep us company as we stood to arms. Under a pale moon, one could just see the grave-like rise of ground which marked the German trenches two hundred yards away. Fires in the English lines had died down, and only the squelch of the sodden boots in the slushy mud, the whispered orders of the officers and the NCOs, and the moan of the wind broke the silence of the night. The soldiers' Christmas Eve had come at last, and it was hardly the time or place to feel grateful for it.
Memory in her shrine kept us in a trance of saddened silence. Back somewhere in England, the fires were burning in cosy rooms; in fancy I heard laughter and the thousand melodies of reunion on Christmas Eve. With overcoat thick with wet mud, hands cracked and sore with the frost, I leaned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trench, and, looking through my loophole, fixed weary eyes on the German trenches. Thoughts surged madly in my mind; but they had no sequence, no cohesion. Mostly they were of home as I had known it through the years that had brought me to this. I asked myself why I was in the trenches in misery at all, when I might have been in England warm and prosperous. That involuntary question was quickly answered. For is there not a multitude of houses in England, and has not someone to keep them intact? I thought of a shattered cottage in -- , and felt glad that I was in the trenches. That cottage was once somebody's home.
Still looking and dreaming, my eyes caught a flare in the darkness. A light in the enemy's trenches was so rare at that hour that I passed a message down the line. I had hardly spoken when light after light sprang up along the German front. Then quite near our dug-outs, so near as to make me start and clutch my rifle, I heard a voice. there was no mistaking that voice with its guttural ring. With ears strained, I listened, and then, all down our line of trenches there came to our ears a greeting unique in war: "English soldier, English soldier, a merry Christmas, a merry Christmas!"
Following that salute boomed the invitation from those harsh voices: "Come out, English soldier; come out here to us." For some little time we were cautious, and did not even answer. Officers, fearing treachery, ordered the men to be silent. But up and down our line one heard the men answering that Christmas greeting from the enemy. How could we resist wishing each other a Merry Christmas, even though we might be at each other's throats immediately afterwards? So we kept up a running conversation with the Germans, all the while our hands ready on our rifles. Blood and peace, enmity and fraternity - war's most amazing paradox. The night wore on to dawn - a night made easier by songs from the German trenches, the pipings of piccolos and from our broad lines laughter and Christmas carols. Not a shot was fired, except for down on our right, where the French artillery were at work.
Came the dawn, pencilling the sky with grey and pink. Under the early light we saw our foes moving recklessly about on top of their trenches. Here, indeed, was courage; no seeking the security of the shelter but a brazen invitation to us to shoot and kill with deadly certainty. But did we shoot? Not likely! We stood up ourselves and called benisons on the Germans. Then came the invitation to fall out of the trenches and meet half way.
Still cautious we hung back. Not so the others. They ran forward in little groups, with hands held up above their heads, asking us to do the same. Not for long could such an appeal be resisted - beside, was not the courage up to now all on one side? Jumping up onto the parapet, a few of us advanced to meet the on-coming Germans. Out went the hands and tightened in the grip of friendship. Christmas had made the bitterest foes friends.
Here was no desire to kill, but just the wish of a few simple soldiers (and no one is quite so simple as a soldier) that on Christmas Day, at any rate, the force of fire should cease. We gave each other cigarettes and exchanged all manner of things. We wrote our names and addresses on the field service postcards, and exchanged them for German ones. We cut the buttons off our coats and took in exchange the Imperial Arms of Germany. But the gift of gifts was Christmas pudding. The sight of it made the Germans' eyes grow wide with hungry wonder, and at the first bite of it they were our friends for ever. Given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Christmas puddings, every German in the trenches before ours would have surrendered.
And so we stayed together for a while and talked, even though all the time there was a strained feeling of suspicion which rather spoilt this Christmas armistice. We could not help remembering that we were enemies, even though we had shaken hands. We dare not advance too near their trenches lest we saw too much, nor could the Germans come beyond the barbed wire which lay before ours. After we had chatted, we turned back to our respective trenches for breakfast.
All through the day no shot was fired, and all we did was talk to each other and make confessions which, perhaps, were truer at that curious moment than in the normal times of war. How far this unofficial truce extended along the lines I do not know, but I do know that what I have written here applies to the -- on our side and the 158th German Brigade, composed of Westphalians.
As I finish this short and scrappy description of a strangely human event, we are pouring rapid fire into the German trenches, and they are returning the compliment just as fiercely. Screeching through the air above us are the shattering shells of rival batteries of artillery. So we are back once more to the ordeal of fire.
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
John Cleese 好幽默
記得三年前
還是四年前
John Cleese (蒙提·派森 Monty Python 的一員)四處巡迴演出
(當時 他剛離婚 需要給前妻一筆龐大的贍養費
快破產的他 不得不演出)
快破產的他 不得不演出)
他來到了愛丁堡
我去看了
他依舊這麼幽默
這一個多鐘頭的輕鬆談話 so funny!!! Enjoy it!
(沒錯 他可是公認英國最幽默的喜劇演員......)
2014年11月21日 星期五
馬格利特, 生日快樂!
1898年的今天,畫家馬格利特出生了! 馬格利特,生日快樂!
若問夢境與現實之間的轉換,表現最好的藝術家是誰?於我,非畫家馬格利特莫屬了.....
為什麼他的畫,經常有人物蒙著一條白布? 我在新書《愛‧邂逅》裡有觸及到這個部分,在此,與你,我的讀者,分享囉......
.... 這位來自比利時的魔術師,作品中充滿迷惑,經常出現夢境的意象,平時可見的物品被他引到畫裡,落在一個奇怪的空間,讓人感覺既錯愕又詼諧,他這樣不斷地玩弄視覺,得歸咎於一段童年不可言說的記憶。
小時候,他母親常鬧自殺,父親沒辦法,只好把她關在房裡,鎖起來,有一晚,不知怎麼的,她走到地窖,栽進水缸,企圖淹死,之後被發現,救了上來......
1912年,他還不到十四歲,媽媽又逃出去,這次是真的,再也沒回來了,幾天後,她的身體在桑布爾河(River Sambre)附近找到,旁邊有一座橋。據說,馬格利特目睹媽媽不動、冰冷的樣子,她的臉被睡衣蓋上,卻光著下身。種種不安的畫面,始終在他腦海,甩也甩不掉。
每次作畫,不歡的影像很容易跑進來,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作品中常有門、門把、鎖頭、籠子等等幽禁的空間。有時候,一扇被擊破的門,是媽媽逃走後,留下的痕跡;有時,一件長袍睡衣,懸在那兒,是她出走,臨終前穿的;有時,一條河與斷一半的橋,是她溺水的現場;有時,一盆水缸,裡面裝滿了水,是她夜晚偷偷到地窖所見的景象;有時,是一些人物,頭部被一條白布遮住,是她死時的模樣。馬格利特畫的,大多示出了母親自殺的證物,對他來說,這段記憶是內心最深沉的隱痛啊!
馬格利特來來回回,在現實與錯覺之中跳來跳去,完全反映了他那不堪的過去,一直在「希望母親活著」到「知道母親已死」之間做持續地交錯、移轉。自然地,圖像會浮出無數的挑釁因子,不過在那兒,我們看不到一點醜陋,是因為親人走時,沒看到臉上的慘狀,那白布的掩飾,保留了一份尊嚴,一份不可說的神祕,因此,他的畫就從痛裡,昇華了起來,最後,目睹的盡是美,飛升的美。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一輩子的追求 (下)
我們對一個藝術家的了解不在一時,而是一輩子的追求。(下)
http://showwe.tw/news/news.aspx?n=189
l 我想提到藝術,不免有讀者會有一些疑問(其實是我自己),
其實,這些藝術大師們遺留偉大的作品,不是要我們愧疚,
你問:看一幅畫該去看什麼?又該怎麼樣欣賞它?
說真的,沒有一定的答案,看一張畫,不論用什麼角度或觀點,
l 卡夫卡曾說:「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
你說的沒錯,這些文豪的名言,是他們的深沈體會後的結語,
有趣的是,以前在台灣,閱讀外文書時,
老實說,那些名言對我影響有多少,我不知道,但它們蠱惑了我,
l 最近正巧訂購了一本有關藝術的書籍,書名為《騙倒買家!:
有啊,這是一本娛樂書,讀來像一部小說,作者肯.派雷尼(Ken Perenyi)引用一位紐約收藏家的話:「
自古以來,人就愛收藏物品,而藝術品又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不過,我還是認為,靠好的藝術史學家的研究、科技的發明、
l 書寫中文的滋味?
說到中文,我在愛丁堡講中文的機會很少,
我的英文,聽說讀寫都十分流暢,但「書寫中文」對我來說,
我的讀者,謝謝你。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情書一事
最近
在念蘇俄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給薇拉的信》(Letters to Véra)
寫了一疊厚厚的信
都是作家與妻子薇拉在幾次短暫分離時寫的
他們超過半世紀的婚姻
真正的幸福是在
百分之九十九在一塊的時光
讓我想到
十四年前
我與P初識時
我們漫步在公園
我問:你現在寫什麼?
P回:我正在撰寫某某人的傳記?
我:進行得如何?
P:很困難?
我:為什麼?
P:這個人是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巨人, 但我很難挖掘他的私生活, 他與妻子沒寫過一封情書, 他們一生都陶醉在幸福的婚姻裡.....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慢慢談了一些自己
我一直愛談別人的作品
 別人的故事
別人的故事 不怎麼愛談自己
這回
出版社訪問了我
我慢慢談了一些自己......
分成上下兩集,上集是「旅行」與「愛丁堡」,下集是關於「藝術」與「文學」的部分。
以下是上集
http://showwe.tw/news/news.aspx?n=188
l 首先,我想可以搭配老師的新書,為讀者帶來一場「歐洲文藝之旅」
旅行,於我,有兩種意義,一是你茫然,
這樣漂泊,或許隱隱的叛逆,
當然,我依然瘋狂詩人、文學家、藝術大師,偶爾的大展,

每個城市,可以只是平平庸庸的,但若有天才出現,
回溯自己旅行的經驗,每到一個地方,也沒什麼目標或目地性,
我喜歡超現實創始者布勒東在路上的閒晃,我喜歡他說的「機遇」(
一開始幾個人先啟話題,我好奇地聽,半個多鐘頭後,我開口了,
現在,我住的愛丁堡,每天的呼吸、思考、談話,每天經過的、
l 老師住過被稱國「英國世界遺產」的愛丁堡,
我常跟人說笑,我家有兩座大花園,前院是草地大公園,
就這樣,我再也沒離開過這個地方。
在這地方,從一開始的陌生,到現在的熟悉,如今,我的看,
這兒,多寒冷,風雨變幻得很歇斯底里,就這樣,我從不感到枯燥,
愛丁堡的藝術季,大概從五月開始,先是電影節,延續下來,
沒錯,愛丁堡是一個能一直給你靈感,補充能量的地方,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薇拉的迷惑
法國有一句諺語:他閃耀 是因他的缺席 (il brille par son absence)
這是我在讀 《給薇拉的信》 (未經刪減 我喜歡這種 uncut)
時所感受到的 薇拉的閃耀!
時所感受到的 薇拉的閃耀!
薇拉在早期 也有她在文學上的創作
很聰慧
但碰到納博科夫之後
她知道納博科夫是一位天才
將成為時代最偉大的作家
所以 她放棄原有的野心
伴著他
很聰慧
但碰到納博科夫之後
她知道納博科夫是一位天才
將成為時代最偉大的作家
所以 她放棄原有的野心
伴著他
她 成為他生命的全部
當納博科夫把《Lolita》手稿扔到火裡燒
是她 把它拯救起來
是她 把它拯救起來
也因為她
他慢慢摸索自己在文學上能做 與不能做的
他慢慢摸索自己在文學上能做 與不能做的
也因為她
他原有的憂鬱與病痛 幾乎要逼他自殺
但他寫信告訴她 因為有她 他無法使出這可怕的行徑
他原有的憂鬱與病痛 幾乎要逼他自殺
但他寫信告訴她 因為有她 他無法使出這可怕的行徑
他們的相遇 是在1923年的一個化妝舞會上
當時 他是一位使用假名的作家
她呢?戴著一個黑色的面具
兩個都很神秘 都在偽裝
當時 他是一位使用假名的作家
她呢?戴著一個黑色的面具
兩個都很神秘 都在偽裝
但從那刻起
直到1977年納博科夫死時
成為史上最恆久與最多產的文學伴侶之一
直到1977年納博科夫死時
成為史上最恆久與最多產的文學伴侶之一
2014年11月4日 星期二
愛‧邂逅──不可不知的17位西方經典藝文大師
我的新書
愛‧邂逅──
不可不知的17位西方經典藝文大師
(November 2014)
想跟我的讀者
告知
我十一月中旬
將會出版一本書
書衣與書名就在上方
書衣有高更的畫
我不知道為什麼出版社要用這張當封面
不過
我很喜歡
我問
是因為裡面寫了十七位藝術家與文學家
裡面有一些精彩的圖片
怎麼特別這一張呢
之前我出了兩本高更書
已用過他的畫了
希望這本有一種新的以前沒用過的圖片
雖這麼說
我還是很愛
因為這張大概是高更最滿意的話
一來他娶了大溪地的美嬌娘
二來他想用它
激起丹麥的妻子的嫉妒
我出生於臺北
自1990年代末
來到了歐洲
從一開始的陌生
到現代的熟悉
如今
我的看
我的呼吸
我皮膚的感覺
愛丁堡的一切
對我是多麼自然
我想
我已經脫離了之前尋找天堂的苦澀
是的
我親吻了天堂
但不代表我藝術生命結束了
反而
因豐盈 我有另一個新的開始
不為野心而寫
不為憂慮而寫
但我想回溯
但我想揭發那淺意識的騷動
但我想探尋長久以來我怎麼忘卻東方的習性 拋棄過去 以不回頭 望向未來
好久
也不怎麼吃中國菜
講中文?
只能利用每天短短的一個小時
跟媽媽講越洋電話 才會用到
我的英文雖流暢
但 “書寫中文”
是一種魔力
又像某種的糾纏
我將 “它” 放在家裡的一個隱私的角落
沒錯
“它” 是我所愛的
也是我在愛丁堡的一個秘密
關在書房裡
開始獨白 開始對話
我也知道遠方
我的讀者
不論是熟人
是陌生人也好
我知道
我一點也不孤單
******
視覺與味道是可以記憶的。
我怎能忘記,跟啟蒙份子的邂逅呢?每每在咖啡館裡,
在那兒,我遇見了藝術與文學大師靈魂,他們騷動著,
此刻,那魂魄又浮現,氣味也飄來了,現在,我知道,那是靈感與原
噢,我看,我聞,我存在。
******
泰納先生
昨天
我去看了一部最新,很受歡迎的電影 -- 泰納先生 (Mr Turner)
(電影院爆滿,要事先訂票)
大概是原來期待很高
又讀到許多影評人寫的影評,多數的報紙評五星
看了之後
有一些些失望
不過,我還是要說
綠景,海景,日出日落,山景
繪圖,素描,水彩畫,油畫 ..... 真是美呆了
演員的演技,特別飾演畫家泰納這位,簡直無可挑剔
沒錯
史實的研究很徹底
但
導演將一些泰納的故事拼湊起來
卻沒有對中心主題做衍生與深入的演化
因為這就像人換氣一樣
為了讓人呼吸的更順暢
需要添入更多的氧氣
或者說一個事件的發生
沒交代前因後果,也沒下文
就又另一個個事件接踵而來
給觀者一種迷失感
電影沒滲透到泰納的心理底層
他對繪畫野心
他性格怪異
他跟父親同住
他捕捉時事的能力
他跟女子的關係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也沒交代
(我認為一切跟他母親瘋掉
從小沒得到一絲母愛有關
這是他一生的秘密
也是他的最苦最痛)
這次
我與一群朋友去看
還好 我們去之前
對泰納的背景做了功課
還能跟著電影走
否則
若對這位畫家不熟的人
看時,真會不知去向
不論戲劇或電影
我認為有一個元素很重要
那就是為每個角色慢慢地築起鮮明的性格
情緒的量與濃度也要漸漸增強
直到快結束前
給予一種高潮與驚奇
這樣
觀者在看完電影時
有種難離開現場
才能頻頻回味
但泰納先生這部電影
大概兩個多鐘頭,以現代電影來說還算長
若用文字來比喻
我認為用了太多的句點
缺乏了逗點
沒有好好的延續與發展
但讓我持續看完的原因
是一幕幕美麗的景象
與我對畫家泰納藝術的忠誠
抱歉
我只能給這部電影三星半!
(別說我吝嗇,這是我看完後的直覺)
一個國家以上
你問我,
來自東方,身處西方,有沒有碰到文化難題?
來自東方,身處西方,有沒有碰到文化難題?
這讓我想到
出生伊朗,在威爾島與瑞士長大、受教育
之後在倫敦定居的一位詩人咪咪˙卡綠阿蒂
寫的一首〈寫信〉:
出生伊朗,在威爾島與瑞士長大、受教育
之後在倫敦定居的一位詩人咪咪˙卡綠阿蒂
寫的一首〈寫信〉:
「國家
我們又開墾,再否認,陷入之間的
兩個字母」
我們又開墾,再否認,陷入之間的
兩個字母」
「國家」一詞,她用了複數
字母與字母之間
在詞彙裡
流竄了五味雜陳
在詞彙裡
流竄了五味雜陳
但說真的
在兩個或以上的國家生根
均受多種文化的影響
內心總拉拉扯扯
有時交戰,有時冷漠,有時撕裂
但有時和解,
就這樣
生命有了張力,精彩、豐富
蹦的火花,更特別,不是嗎?
在兩個或以上的國家生根
均受多種文化的影響
內心總拉拉扯扯
有時交戰,有時冷漠,有時撕裂
但有時和解,
就這樣
生命有了張力,精彩、豐富
蹦的火花,更特別,不是嗎?
註:
咪咪˙卡綠阿蒂(Mimi Khalvati)
〈寫信〉(“Writing Letters”)
咪咪˙卡綠阿蒂(Mimi Khalvati)
〈寫信〉(“Writing Letters”)
訂閱:
文章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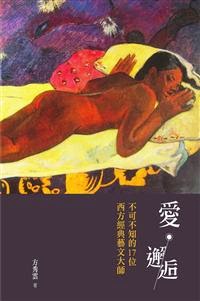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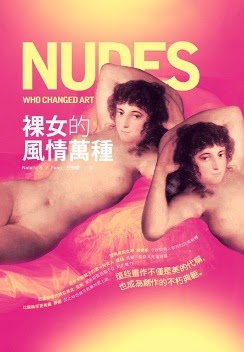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