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
女人的愛情與生命
一位在奧地利的友人介紹我聽舒曼的歌曲集 <<女人的愛情與生命>>
(Schumann: Frauenliebe und -leben, Op. 42)
聽了之後, 我動容不已....
Seit ich ihn gesehen (Since I Saw Him)
Er, der Herrlichste von allen (He, the Noblest of All)
Ich kann's nicht fassen, nicht glauben (I Cannot Grasp or Believe It)
Du Ring an meinem Finger (You Ring Upon My Finger)
Helft mir, ihr Schwestern (Help Me, Sisters)
Süßer Freund, du blickest mich verwundert an (Sweet Friend, You Gaze)
An meinem Herzen, an meiner Brust (At My Heart, At My Breast)
Nun hast du mir den ersten Schmerz getan (Now You Have Caused Me Pain for the First Time)
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誰來晚餐?
從一齣舞台劇帶起....
說牛頓用光譜來分析彩虹,扼殺了浪漫的情懷,完全破壞彩虹的詩性,年少的濟慈心有戚戚焉,最後,他們一起向「牛頓的數學混濁」敬酒。這餐宴過程被漢頓紀錄了下來,還取了一個名字──「永恆的晚餐」……
我在聯合副刊的<誰來晚餐?>, 說浪漫... 猜猜, 我邀請誰來晚餐?
http://udn.com/NEWS/READING/X5/8412808.shtml
說牛頓用光譜來分析彩虹,扼殺了浪漫的情懷,完全破壞彩虹的詩性,年少的濟慈心有戚戚焉,最後,他們一起向「牛頓的數學混濁」敬酒。這餐宴過程被漢頓紀錄了下來,還取了一個名字──「永恆的晚餐」……
我在聯合副刊的<誰來晚餐?>, 說浪漫... 猜猜, 我邀請誰來晚餐?
http://udn.com/NEWS/READING/X5/8412808.shtml
 |
|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國詩人、畫家)畫作〈牛頓〉。畫中牛頓裸身坐在水藻滋蔓的岩石上,顯然是海底景象,他蜷伏著,全神貫注地在紙捲上,用尺規畫三角形與半圓。詩人布萊克反對牛頓的光學理論,在〈拉奧孔〉(“Laocoon”)畫上,寫著宣言:「藝術是生命之樹;科學視死亡之樹。」 |
走出愛丁堡的解剖戲院,站在中庭,突然襲來一陣涼風,抬頭,看見了滿天的星星,我跟L說:真棒!剛剛好像在跟一群巨人共餐飲酒呢!
L反應:這不就如柏拉圖的饗宴嗎?
我回答:是啊!柏拉圖的饗宴,一些人在雅典談愛;而這兒,他們談牛頓……
甩出的七彩
在《牛頓》劇的舞台上,沒有複雜的道具,只有一台望遠鏡、兩把椅子、與一條絲巾,單單這樣,就演得很精采了。
這位莎士比亞舞台劇的演員,將三百多年來跟牛頓扯上關係的人物,包括詩人謝爾蓋(Serguei)、西柏(Colley Cibber)、科學家愛因斯坦、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哲學家胡克(Robert Hooke)、政治家邱吉爾、短跑健將柏爾特(Usain Bolt)……等等約十多人,全引了進來,一個人飾演全部的角色,摻入不同的觀點,一一述說這位科學家的不朽傳奇。
為何精采?在於那對話與獨白。
落幕時,演員將身上的那一條黑絲巾,一甩,甩成了七彩。
彩虹的象徵
此七彩,象徵自然界的「彩虹」。相信你我都經歷過雨後天晴,天空畫出一道彩虹,染上的興奮心情吧!在中國神話裡,它是女媧煉色補天,發出的彩光;在台灣原住民心中,那盡頭是祖靈的住處;北歐的神話,是神與人類之間的溝通要塞;希臘神話,它化作女子,成了天上與人間的使者;而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經典呢?代表上帝對諾亞與後代的允諾,不再降洪水。
或許每個族群,自古對彩虹的解讀不同,但卻有那麼一個共通性──七彩叩門,搖撼了無度的想像,許多故事、詩、小說,與藝術作品,從此問世。
筵席與之後
自有人類以來,世上不知有多少的餐飲宴?藉吃吃喝喝,盡興而歸,應不計其數吧!然而,能引起思想衝擊,遠遠流長,讓後代記憶的,又有幾個呢?柏拉圖的饗宴,我想,大概最聞名的了,參與的有貴族、律師、醫生、劇作家、悲劇詩人、哲學家、政治人物……各有專業,經驗、思索不同,奧妙的是,他們的對話與獨白,之迷惑,兩千多年來,已成為興致勃勃文藝沙龍的原型了。
話說19世紀,有一場類似的筵席,發生在1817年12月的一個晚上……
聖誕節一過後,畫家兼日記作者班傑明‧漢頓(Benjamin Haydon,1786-1846)辦了一個聚餐,為了介紹濟慈(John Keats,1795-1821)給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認識,這一少一中的浪漫派詩人來了,那晚,到訪的賓客還有劇作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紳士兼商人芒克浩斯(Thomas Monkhouse)、外科醫生兼探險者瑞奇(Joseph Ritchie)與審計官員金斯頓(John Kingston)。
用餐時,他們即興地演說荷馬、米爾頓(Milton)與維吉爾(Virgil)的史詩,及莎士比亞劇,有一時刻,華茲華斯飾演莎劇的李爾王,語調有些嚴肅,蘭姆喝醉酒,變得瘋瘋癲癲,想逗他,話鋒一轉,轉到了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接著,不知怎麼的,扯到了科學家牛頓:
這傢伙除了清楚三角形的三邊,其他什麼事都不相信!
還說牛頓用光譜來分析彩虹,扼殺了浪漫的情懷,完全破壞彩虹的詩性。年少的濟慈心有戚戚焉,最後,他們一起向「牛頓的數學混濁」敬酒。
這餐宴過程被漢頓紀錄了下來,還取了一個名字──「永恆的晚餐」(“the immortal dinner”)。往後,常被文學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
沒多久,濟慈寫下一段:
一切風情盡散
在自然哲學(科學),區區的冰冷之觸?
天際原有一道織錦的彩虹:
我們熟知她的緯線,她的質地;如今,她卻
身列乏味的分門別類一員。
自然哲學讓天使折翼,
以法則與線條,征服神祕,
騰空靈幻氤氳,鏟除寶藏地精──
拆解彩虹,就像片刻前創造的
溫柔人拉彌亞,委身躲入蔭中。
在自然哲學(科學),區區的冰冷之觸?
天際原有一道織錦的彩虹:
我們熟知她的緯線,她的質地;如今,她卻
身列乏味的分門別類一員。
自然哲學讓天使折翼,
以法則與線條,征服神祕,
騰空靈幻氤氳,鏟除寶藏地精──
拆解彩虹,就像片刻前創造的
溫柔人拉彌亞,委身躲入蔭中。
這是〈拉彌亞〉(“Lamia”)第二部分的詩行,因1817年的那頓晚餐,喚起的話題,濟慈私底下,寫了這段獨白,指責牛頓的「拆解彩虹」惡行,也因此,燃點了激辯,兩百年來,人們真掉進了科學與藝術,真實與想像,理性與感性的爭論。
而,在濟慈與牛頓之間,你站在那一邊呢?
紙張的獨白
從小,我沒有留存物品的概念,許多年少的東西,早就不翼而飛了!但,有幾張紙片,一直捨不得丟。
早期,我念工程,極喜愛數學與物理。約十八歲那一年,一個冷颼颼的夜晚,我獨自在陽台上,從鐵窗望去,眼前一棟棟的高樓大廈,與夾雜的廣告看板,很典型的台北景象,最適合作夢了。那一刻,小腦袋展翅,飛到了另一個時空,想的竟是光與色,興興然地,我從屋內拿出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盞檯燈、一枝筆與一些白紙……
在陽台,就這樣坐著,開始用複雜的微積分,偵視光線的折射與反射的角度,探索光與彩虹的關係,幾個小時,全神貫注,結果,把光譜七彩的數據,全運算出來了,當刻,我有一份狂喜,似乎掘出了一個祕密,僅屬於我與宇宙之間。
那一剎那,我與美麗的顏色相遇了。
此驚奇,就這樣發生在我身上,一年一年過去,還在我心頭迴繞,漢頓「永恆的晚餐」最後一句:
受孤獨之佑,在那內向之眼上,永恆地發光。
讀到這,沒錯,猶如這般觸動。
說來,那幾張充滿數學符號的紙片,在我出國留學那一年,連同我的第一本詩集,送給了一位愛物理與文學的男孩。那些符號,當然是真理的印記,閃爍的卻是最美、最浪漫的獨白。
女媧上色
何謂彩虹?若查百科全書,會描述:氣象中的一種光學現象,當陽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珠,光線被折射及反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彩的光譜……。嗯,好像缺少了什麼?
一位久遠前的蘇格蘭詩人兼劇作家詹姆斯‧湯普森(James Thomson,1700-48)了解理性若不小心,會墮入浪漫的貧瘠,於1727年,寫下〈獻給記憶牛頓的詩〉,添補了:
……
甚至現身的光,本尊
隱藏地照耀,直至機敏的心智如他
不拆解裹亮的日袍;
而,從白化的不明大火
吸吮每道,入了天性,
到了媚眼,喚醒行列之醉
原色啊!開啟焰紅
活潑地跳;接下褐菊;
再迎可口黃;之旁呢?
落下綠的全鮮,柔柔光束。
然後純藍,湧了秋樣天
縹緲地揮灑;試試一些悲調
浮靛藍,游深邃,正值
黃昏濃得化不開,與霜低垂;
當折射光的閃爍尾巴
駐足微微的紫羅蘭,漸漸消失。
這些呢?當雲提煉沉醉之浴,
射出朝下的淋淋之弓;
我們頭頂,濕露幻影屈身
愉悅地,溶化到田野下。
一萬的混染揚起,
而一萬依舊--泉源無盡
美,何曾豐盈,何曾新穎。
隱藏地照耀,直至機敏的心智如他
不拆解裹亮的日袍;
而,從白化的不明大火
吸吮每道,入了天性,
到了媚眼,喚醒行列之醉
原色啊!開啟焰紅
活潑地跳;接下褐菊;
再迎可口黃;之旁呢?
落下綠的全鮮,柔柔光束。
然後純藍,湧了秋樣天
縹緲地揮灑;試試一些悲調
浮靛藍,游深邃,正值
黃昏濃得化不開,與霜低垂;
當折射光的閃爍尾巴
駐足微微的紫羅蘭,漸漸消失。
這些呢?當雲提煉沉醉之浴,
射出朝下的淋淋之弓;
我們頭頂,濕露幻影屈身
愉悅地,溶化到田野下。
一萬的混染揚起,
而一萬依舊--泉源無盡
美,何曾豐盈,何曾新穎。
……
好個「不拆解」!詩人湯普森是一位自然哲學的信仰者,塗上的這道彩虹,一色接一色,溢滿了想像的蠱惑,不是嗎?
有時,觀看新聞,因衛星照相,呈現一幕幕從外太空傳來的畫面,星球上的乾枯,如一堆堆的岩塊,一片片的沙漠,然而,這些怎麼也無法阻擋我們天馬行空的幻想,就如,我看完《牛頓》劇後,在中庭,望向滿天的星星,心想,哪一顆是小王子走過的星球呢?尋找著,隱約,還聽到他歇斯底里的笑聲,更激動地,想衝去跟飛行員聖埃克索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小王子》的作者)報告,說:我找到你失散已久的寶貝了。
不再迷信,不再無知,一個毫無恐懼的幻象,存在的詩性,會更深、更美、更真。曾幾何時,我遇見了彩虹,或許飄來一些數學符號,但胸中,湧現的卻是溫柔的女媧,補天時煉出的彩光啊!
探索浪漫的藝術是美,追尋真理的科學呢?沉思已久的濟慈,終於在1819年之春譜下一首〈希臘古甕〉(“Ode on a Grecian Urn”),以最末兩句做了回應: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那是所有
你在世上知道,和所有你必須知道的。
你在世上知道,和所有你必須知道的。
我常想,自己始終被那藝術中充滿多彩的顏色所吸引,這麼愛「色」,難道是十八歲那年陽台上的獨白嗎?
理性與浪漫的和解
原來,我在年少時,已演出了一場舞台劇,那兒,沒有複雜的道具,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盞檯燈、筆與紙……
今晚,我準備了一些酒菜,邀請濟慈、湯普森、布萊克、與牛頓一塊用餐,我的讀者,來當我的座上賓,咱們一起向「理性與浪漫的和解」敬酒,如何?
訂閱:
文章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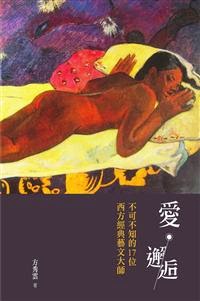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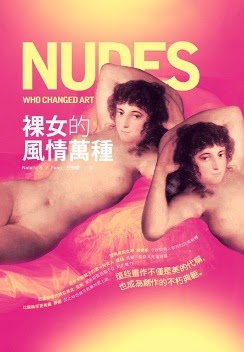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