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 007 又來了
今年是《惡魔四伏》(Spectre)
跟前一部一樣
同是 Daniel Craig 扮演 007
我總覺得
他樣子太過於冷漠了
我想,這並非原創者 Ian Fleming 的初衷……
*****
1952年,一位來自英國的前海軍情報員兼記者伊恩‧弗列明(Ian Fleming,1908-1964)在牙買加度假時,於海邊的別墅,一早坐在桌前,三個小時內,不經思考地,寫下了兩千多字,就像繆斯搖動他筆桿似的,六十天後,完成《皇家賭場》(Casino Royale)書稿,於是,007的角色誕生了,他名叫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
主角勝於小說家
賭場、馬丁尼酒、貝瑞塔手槍、殺人的機關配件、創意造型車子、神祕女郎、海底潛水、打鬥場景、英雄救美、維護國家安全、伸張正義、擊敗邪惡……這些,對你我來說,是否似曾相識呢?它們都成了007故事不可或缺的元素。
自1962年由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飾演《諾博士》(Dr. No)之後,幾乎每一、兩年有一部007的電影,從未間斷,到今年已是五十三周年!這刺激、驚悚的故事與鮮明的角色怎麼來的呢?雛形,於1940年代初期,就塑造出來了,當時,弗列明對戰爭的緊張情緒,對敵國起了偏執狂,對間諜身兼的任務,對身邊友人的觀察,這些細節,他相當熟悉,再添上自己的習性與瘋狂的夢想,一個英雄的特殊性格與周遭的配套,持續在弗列明的心裡盤繞,幾年後,便洋洋灑灑的鋪陳了出來。
當他完成《皇家賭場》時,說了:「糟透、愚蠢的作品!」似乎不太滿意,還將稿子拿給情婦看,讀後,她建議他不要出版,若真要出,用假名,否則玷汙了他的名聲。別說他們,連出版社也不看好,後來,是因他哥哥(知名旅遊作家)的介入,才得以問世,書一出來,馬上銷售一空,跌破了專家眼鏡。間諜角色一旦釋放,弗列明再也停不下來了,每年初春,一定好好坐下來,以密使為原型,花兩個月書寫一本,如此下去,直到過世為止,一共十四本完稿,十分之六世紀以來,他發明的007風靡了全球,早已成普遍性的文化現象,那燃燒的魅力,怎麼也消不退。
或許你沒聽過弗列明,但一定聽過007,當故事主角的聲譽,遠勝於小說家,我想,就算寫作成功了。
慾望的反射
間諜有什麼特質呢?一般而言,一定被抓到什麼把柄,或有難言之隱,害怕被揭發出來,情報局利用的就是這種人性弱點,來聘雇員工的,之所以當間諜,通常是不得已的,他們的長相越不起眼越好,總之,普普通通,不至於讓人起疑心。然而,007被量身訂做後,完全變了個樣,他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受好的教育,一身運動細胞,鍛鍊強健的體魄,不但長得帥,懂得穿著,突出的性格,一走出來,全部的目光都往他身上掃,這般耀眼,若真的來當間諜,不就立刻被識穿了嗎?
雖然弗列明戰爭期間擔任情報員,但,是待在辦公室那型的,坐在房內,眼見一份接一份的國家機密文件,耳聞許多證實與不被證實的風聲,心裡呢?早已飄飄欲仙了。密使喬裝成另一個身分,到敵國搜尋資訊,必要時,有所行動,因為這一切是不可說的,所以,包裹著一層神祕的外衣,濃烈地,讓弗列明不得不吸進去,即是那未決、煩擾、迷惑力,驅使他用想像來填充,於是,冒險、驚悚的無窮因子,從他的腦袋裡,猛跑出來,他生活中無法實現的缺憾,卻在創作中,找到了特許之地,補償了他,其實啊!他對007是既羨慕又嫉妒。
不必朝九晚五,無須養家,可大吃大飲大賭,常有美豔女子圍繞,所有每日的開銷,不用擔心,上級會義務、毫不吝嗇地,幫他買單,一般人跟他相較起來,生活簡直繁瑣、枯燥,若能選擇,誰不想過他那種逍遙的日子呢!原來,此角色投射的是——嚮往,不僅對作者如此,對多數的人,更是逃不了的慾念啊!
就因007,添入迷人的色彩,一改了間諜的形象。
親吻死亡
要物質,有物質,生活精采歸精采,不過,也有代價要付,那就是性命。
人在面對死亡的威脅,一下子,變得害怕、軟弱,會整個投降,然龐德的反應出乎意外,不但勇敢,更拚命地,直接拿身體去對抗;另外,他愛碰烈酒,弄到常跟人競賽,看誰喝得多,喝得快,同時,也猛抽菸,專抽那種尼古丁特多的品牌,平均量每天六十根,這樣習性,純屬於不要命,那情境,多像哲學家叔本華與心理學家佛洛依德說過的「死亡趨動力」,渴求——如親吻死亡一般。
是的,在弗列明的《你只能活兩次》(You Only Live Twice)裡,談到了龐德的人生態度,有一次,他被派到日本東京執行任務,突然失蹤了,情報局以為他喪生,女上司M撰寫一篇訃告,最末一段是這樣的:
我幸運,也自豪地,在國防部的過去三年,與中校龐德緊密團結、合作共事,對他敬畏,如今他的死,我該怎麼用簡短的語句,來寫墓碑銘呢?這兒許多資淺的同事認為,都分享了他的哲學,那是: 我不應浪費我的日子,也不嘗試延長生命,我應善用我的時間。
龐德沒有所謂長壽的觀念,每一刻,他都要抓住,將生命的目的發揮極限,沒必要為了活著而苟延殘喘,其實,他隨時隨地,在預備死亡啊!
致命傷
我曾想,若龐德沒什麼把柄,沒什麼需要隱藏的,為什麼去當間諜?問題出在哪兒?
弗列明1964年,寫第十二本007小說時,終於打破沉默,給龐德一點人性的描述,揭發了他的出生背景,說他來自蘇格蘭的格倫科(Glencoe),十一歲時,父母登山遇難了,從此成為孤兒……
啊!就是這個事實,他在心裡,起了一個大洞,始終在尋找一種歸屬感,沒有家庭,但祕密情報局願意用他,剩下的只有仰賴國族主義了,他的感激之情,轉化成忠貞的愛國分子,於是,將自己訓練成一個冷血的殺人機器,但這不代表殘酷、暴力,他有原則:從不濫殺,抵抗仇敵時,不從背後襲擊,也不會在對方沒警覺下害人,他所做的,絕對是君子之爭。
他喝烈酒,染菸癮,其實,也是弗列明的習性,更勝的是,他每天抽了八十根香菸,同樣的,也不怕死。關鍵的是,弗列明的父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前線作戰,被炸死了,當刻他才九歲,小小的心靈,卻喚起了一個永恆的英雄形象,而自己呢?從未上過戰場,於他,是個缺憾。發明龐德,填補了他的破洞,陳述的全是內心的寫照。
作者與男主角像同卵雙生,孤兒的原型,成了他們的弱點,也是他們一生的致命傷。
酒的哲學
若殺人時,有原則,那麼龐德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就是一句:「搖,不要攪。」這是他的口頭禪,指的是他在喝馬丁尼酒前,對混酒時的嚴格要求。
在《皇家賭場》第七章〈紅與黑〉裡,龐德、酒保與友人雷特有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一杯苦馬丁尼酒……倒入深的香檳高腳酒杯。」龐德說。
「好的,先生。」
「等一下。三單位的高登琴酒、一單位的伏特加酒、半單位的奎寧香甜酒,好好地搖,直到變得冰冷,然後加一大薄片的檸檬皮。明白了嗎?」
「當然,先生。」酒保似乎滿意這點子。
「天啊,那肯定可喝。」雷特說。
龐德笑了,繼續解釋:「當我……呃……集中精神……我永遠不會在餐前飲超過一杯。我喜歡一杯,但要大,又要很烈、很冷,當然,得精心製作……這飲料是我發明的,若想到好名字,我將申請專利。」
這酒名,最後叫「微絲彭」(Vesper),此是取自於他鍾愛女人的名字。搖晃的,跟攪拌的,差別在哪兒?據說搖的,會冒出較多的抗氧化劑,適度飲用,可幫助健康,然而,龐德對養生沒什麼興趣,所以,不在考慮範圍內,我想,他身為享樂主義者,大概搖晃的馬丁尼酒,暗示震盪巨,溶合力強,味道更好、更濃,重要的是,他相信突來的化學變化。
弗列明為了勾勒出龐德的格調,用飲馬丁尼酒,來說明他的文化、成熟度、智力與品味的高低,還有,藉由酒,弗列明更想強調對女人的態度,或許,我們認為龐德是個花花公子,但不管他怎麼到處留情,基於愛的化學變化,他會將她們從水深火熱的苦難中救上來,一旦許諾了,會履行到底,從不傷人的心,絕不會令人失望。
真實的性格
弗列明曾描述:「龐德……有些冷酷、無情。」也說:「他在嘴裡有一點殘忍,眼冷冷的。」007好幾年來,給人一種冷血的印象,但1964年,弗列明決定,要好好的為他的主角還原本色,賜予他一個真實的性格……
孤兒,成熟了,嘴裡不再含有苦澀,在嘴角邊,露出了機敏的微笑;眼中也不再像復仇那般冷,閃耀的卻是返以回報的多情,那就是,多了一份人性的幽默。
這樣才算性感,才像真正的英雄,不是嗎?
取自我的新書【愛 邂逅】Chapter 13 喝馬丁酒時的搖,不要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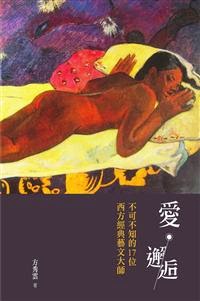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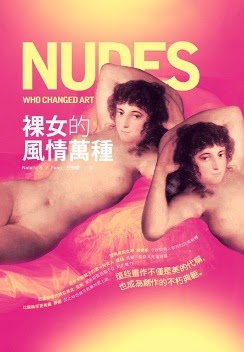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